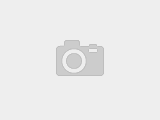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人类社会,远的且不谈,ChatGPT的诞生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乃至毁灭人类的担忧。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永谋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

刘永谋(图源-RUC外哲)
技术带来希望,也同时潜藏着危机。刘永谋教授是一个温和的科学主义者,主张科技谦逊主义。他关注技术的反叛,呼吁大家警惕新科技的治理滥用。
长期关注北大社和北大博雅讲坛的朋友对于刘永谋老师想必并不陌生,对于近年热议的“元宇宙”概念,他从技术、学术、话术与艺术四个方面区分不同的元宇宙叙事,直面元宇宙的挑战,警示可能的“元宇宙陷阱”。

刘永谋老师做客北大博雅讲坛
对于《鱿鱼游戏》所呈现的技术极权的可能,他指出未来科学城邦必然是“介于乌托邦和敌托邦之间”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科技发展水平,未来科学城邦之路不会都一样。
他在人民大学开设的科学哲学课程——“科学技术哲学课程”也深受学生们的喜爱。2020年,在社科院哲学所“《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1989)电子版发布式暨时代变局下的科技与哲学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中,刘永谋教授直言:“科技哲学的好时光到了!倡导同仁介入社会,介入时代变局”。
那么,在期待与忧惧交织的科技新世界, 人类何为?在新科技变局下,当下社会的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又会是什么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永谋教授在新书《科技与社会十四讲》中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01
“我命由我不由技术”
技术时代每个人都是英雄
对于技术新世界,我们关注得并不够,了解得还不多。偏偏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最大特点之一是:它的影响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关于新科技的影响,有人发现:大家总是在短期内高估它们的社会冲击,却往往低估其长期效应。关于新科技的风险,有人发现:在没有充分应用之前,很难预料它们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当新科技风险充分暴露之后,却已经错失控制风险的良机。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未来命运可以归结为在新科技锻造的新世界中冒险。
在我看来,“代达罗斯的迷宫”是技术新世界最好的隐喻。旧世界正在被新世界所取代,确定性正在被不确定性取代,一座“代达罗斯的迷宫”破土而出。在技术时代的舞台上,围绕着新科技迷宫,各色人等的故事和冲突开始上演。

浮雕《伊卡洛斯的坠落》(17世纪作品),现藏法国贡布埃涅市Antoine Vivenel博物馆。画面右下角为代达罗斯建造的迷宫。
代达罗斯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鲁班,因其为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建造迷宫而闻名。他从小就喜欢各种技艺,水平极高。后来,他的外甥跟他学雕塑,他教得很尽心,结果徒弟技术超过师父,名声越来越大,被师父谋杀了。可以说,代达罗斯是一位科技狂人。代达罗斯的儿子叫伊卡洛斯,从小喜欢给父亲帮忙。代达罗斯造出可以飞行的羽毛翅膀,也给伊卡洛斯造了双小翅膀。他告诫儿子不要飞太高,否则太阳会烧坏翅膀,也不能飞太低,海水会打湿翅膀。伊卡洛斯得意忘形,飞得太高,太阳融化翅膀上的蜡,羽毛散了,结果坠落淹死了。
主导技术创新的新科技专家,与代达罗斯一般野心勃勃,其中不少人对新科技发展的未来愿景表现出同样的狂热。
面对新科技突飞猛进,感受到风险逼近的人民,在新科技迷宫中又忧又惧,呼唤着技术时代的忒修斯。
而在新世界舞台的深处,权力如国王米诺斯一样,兴致勃勃地注视着一切,盘算着驯服一切,包括牛首人身的米诺陶诺斯。

忒修斯杀死米诺陶洛斯
那么,谁来扮演英雄的角色,“引领”人民控制新科技?
当下社会的知识分子注定无法脱离新科技的语境。不关心新科技问题,必定远离时代精神,偏居一隅自娱自乐。不关心新科技问题,如何关心人,如何追求美好生活?
必须指出,知识分子的“引领”,并非包办,亦没有能力包办。鉴于新科技问题的复杂性,新科技实践的转变牵一发而动全身,控制新科技以使之为人民服务的伟业,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技术时代,如何自处?由于影响深入个体生活,对新科技发展的社会影响及其应对,大家均非常关心。总之,走出“代达罗斯的迷宫”,必须依靠所有人的力量。
技术时代没有英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在《技术的追问》中,悲观主义者海德格尔说:“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的支配作用归于命运。”技术当真是不可逆转的天命吗?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纠缠于技术可控与失控的思想争论,而是为了控制新科技发展,现在、立刻、马上行动起来。
即使技术真的是天命,记不记得电影《哪吒》中的呐喊:我命由我不由天!东晋的葛洪也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
是的,我命由我不由技术!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为控制技术、为科技向善尽一份力。我以为,这是技术时代知识分子首先要高声传达的声音。
进一步而言,知识分子的“引领”主要是预测、呼吁和建议。所谓预测,指的是对于新科技的社会影响,先行研究,先行估量,冷静审度。所谓呼吁,指的是不断提醒公众可能出现的技术风险,提醒大家不可掉以轻心。所谓建议,指的是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和可行性的风险应对方案,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02
科技使得文化庸俗化?
守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有很多人总认为,网上全是“三俗”内容,黄赌毒也不少见,所以严重阻碍人文发展。此类流行论调,属于由来已久的“两种文化”争论的新形式,即争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否相互对立。“两种文化”概念因斯诺演讲而出名,又被称为“斯诺命题”。事情果真如此吗?互联网阻碍人文发展,科技有害于人文发展吗?我们来深入考察一番。
什么是人文?日常大家讲到人文,一般涉及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宗教等文艺类的“东西”。很显然,对于此类领域的发展,互联网好处多多。
比如说,有了互联网,普通人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取各种文艺资料,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互联网让发表变得很容易。写个日记,编个故事,有很多方法很容易就发表出来。
即使对于文艺的专业研究,互联网也带来极大的便利。首先方便资料传播。其次,互联网改变社会,给人文研究提出很多问题,带来知识生产新的增长点。再次,互联网给人文研究提供新方法。比如数字技术与艺术创作催生数字艺术,用计算机作曲、画画,用计算机写新闻报道、写小说,甚至写诗。因此,从总体上看,互联网利好人文发展,甚至可以说“大大利好”。
有人可能反驳说:互联网繁荣文化是表面的,它助长假人文、伪文化,实际有损人文精神?
互联挑战人文,并非新话题。科学与人文冲突的观点,流传已久。1959年,学物理出身的英国小说家斯诺,在剑桥大学做过一场著名演讲,题目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此后,“两种文化”的术语便广为流传。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
在演讲中,斯诺指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存在文化断裂的现象,引发关于科学与人文在现代社会中功能的大争论。他认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存在彼此不理解的鸿沟,进而滋生出敌意和反感,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均认为对方没有文化,没有社会价值。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两种文化分裂是一大损失,必须把它们融为一体,才能使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过程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使人类社会走向协调发展。
斯诺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美国政要造访剑桥大学,在欢迎晚宴上,校长请来几位大牌教授作陪,结果大家根本没法聊天,校长只好安慰来宾说:这几个教授都是数学家,我们从来不搭理他们!
另一个例子是剑桥著名数学家哈代有一次曾向斯诺抱怨:按照目前“知识分子”一词的用法,他和卢瑟福、狄拉克等科学家,统统被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显然,哈代对人文学者垄断“知识分子”的称号很不满。
在西方文明史上,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不过没有20世纪以后明显。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文理不分家,有教养的人要掌握所谓的“七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语法、逻辑(雄辩)和修辞。
到了中世纪,“七艺”被分为初级的文科“三艺”和进阶的理科“四艺”,教授理科的人开始觉得自己高出文科学者一头。
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者则公开批评理工科研究。在一篇名为《对医生的指责》的文章中,诗人彼得拉克用刻薄的语言挖苦医生:“去干你的行当吧,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否则就杀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么可以干如此卑鄙的勾当,让修辞学委身医学,让主人服侍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于机械的艺术呢?”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
在启蒙运动中,卢梭成为反对科学的典型。在1750年第戎科学院举办的征文大赛中,卢梭夺冠的论文主题是:艺术与科学有害于人类。他认为,科学产生于卑鄙的动机,文明令人腐化,只有野蛮人才具有高尚的德行。这些想法在他1754年的《论不平等》中,被进一步发挥。当伏尔泰收到《论不平等》后,尖刻嘲讽了卢梭。两位启蒙大师从此反目,势同水火。
19世纪以后,现代科技高歌猛进,科学家日益占据上风。1820年,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朋友皮考克发表一篇短文,提出在科技昌明的时代,诗歌已不合时宜。为此,雪莱写下《诗辩》回应,批评功利主义与科学至上的观点。
1923年,遗传学家霍尔丹与哲学家罗素为科学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当时,他俩都在剑桥大学任教。霍尔丹发表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以代达罗斯的故事为隐喻,宣称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在科学探索的路上无须顾忌任何禁区。第二年,罗素发表《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予以回应,借代达罗斯之子伊卡洛斯的故事,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灾难。
霍尔丹的演讲名为“代达罗斯”,暗指科学力量多么伟大,而罗素反驳的演讲名为“伊卡洛斯”,隐喻科学不要太骄傲,小心惹祸。
回到“互联网与人文”问题上,我们的讨论应该深入下去,落实下去。精神层面的讨论大而化之,看起来很高深,对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效果有限。如果非要总结人文精神,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容忍不同意见并存的多元包容精神。
互联网和智能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平台,有志于传播人文的人应该好好利用它,并且要随时警惕利用科技手段压制不同声音的举动。
03
AI会让人类失业吗?
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 AI 失业只会愈演愈烈,“经济奇点”迟早要到来。AI 迟早要取代人类绝大部分的劳动,而这本身就是 AI 发展的根本性目标。有人担忧,此时绝大多数人不能创造 GDP,会不会成为智能社会中“无用的人”。

但是,能够取代并不等于实际取代,这牵涉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机器人可以让所有人都很少劳动或不劳动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但有些人不希望其他人不劳动,想继续通过社会制度强迫其他人劳动,掠夺其他人,压迫其他人。这一点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史发展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因此,AI 失业问题涉及制度变革,光靠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永远解决不了。对不对?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让科技红利尤其是 AI 红利惠及所有人,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少数人。
当然,“AI 失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考虑远景和现实两方面情况。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远景中的理想,而现实中的社会制度进化需要很长的时间,既要等待 AI 科技的不断发展,也要考虑在社会容忍的范围内稳妥地前进。在现实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努力:第一帮助受到 AI 冲击的劳动者找到新工作岗位,能够分享先进科技生产力创造的物质财富;第二要持续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给人类更多的闲暇时间。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得益于科技之力量,压在人类身上的劳动负担越来越轻。20 世纪我们搞了 8 小时工作制,后来又是 5 天工作制、带薪休假制。既然 AI 将替代人类劳动,为什么不能允许社会成员拥有大量闲暇,非要通过制度安排逼迫大家都“996”呢?最近,美国加利福尼亚立法机构提出一项提案,要将一周 5 天工作制改为 4 天工作制。
在《信息崇拜》一书中,罗斯扎克嘲笑说,计算机的发展史同时是一部计算机科技人员的“吹牛史”,什么超级智能、“数字永生”、超越人类等全是“吹牛”。为什么要“吹牛”呢?他一针见血地说:“人工智能研究进行下意识的自我吹嘘的原因十分简单:大量的资金注入了这项研究。”但是,他和维纳一样非常担心“AI 失业问题”。
技术时代,如何自处呢?这是一个与每个人相关的问题,值得每个人认真思考。与其担忧超级智能压迫人类,不如现实一点关心一下 AI 对劳动人民的冲击。